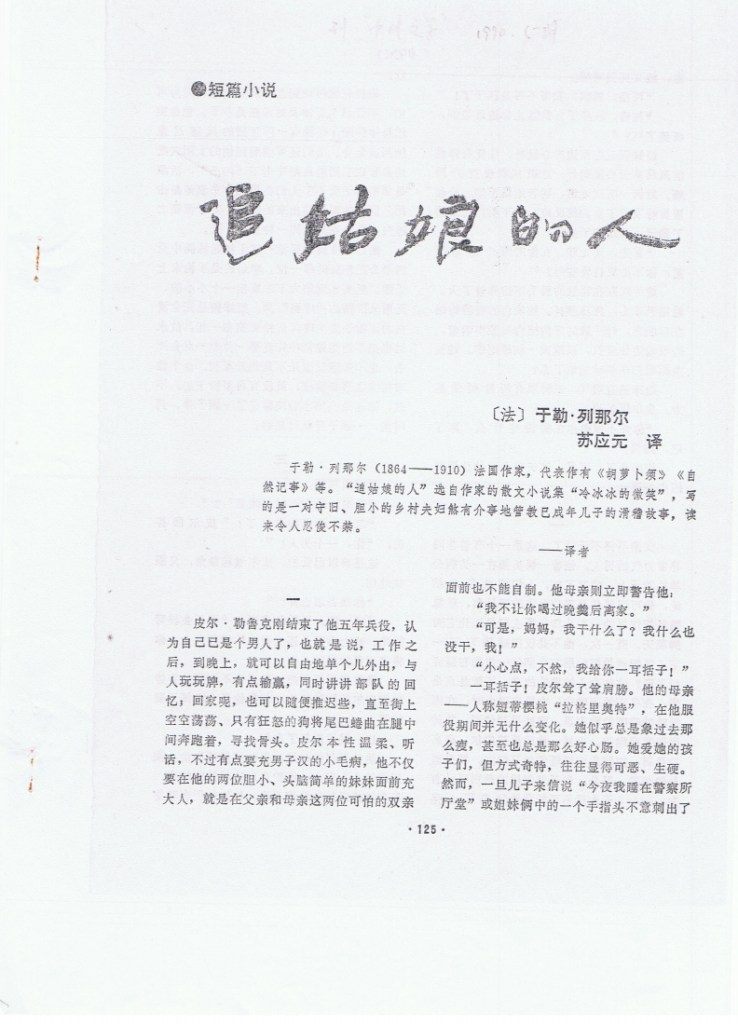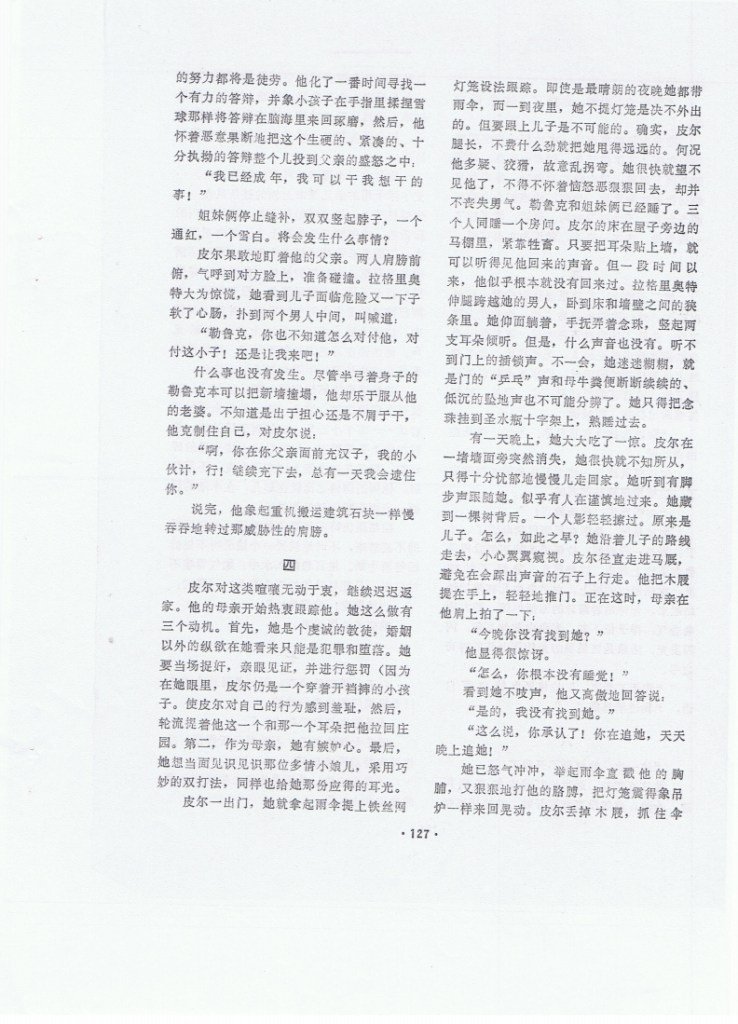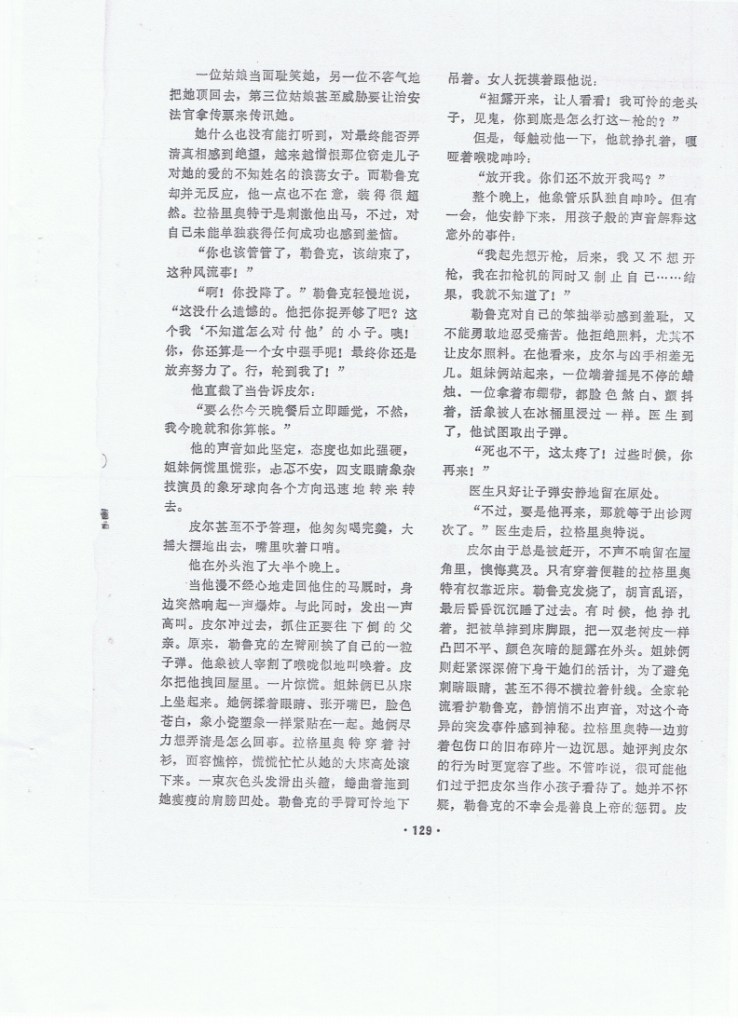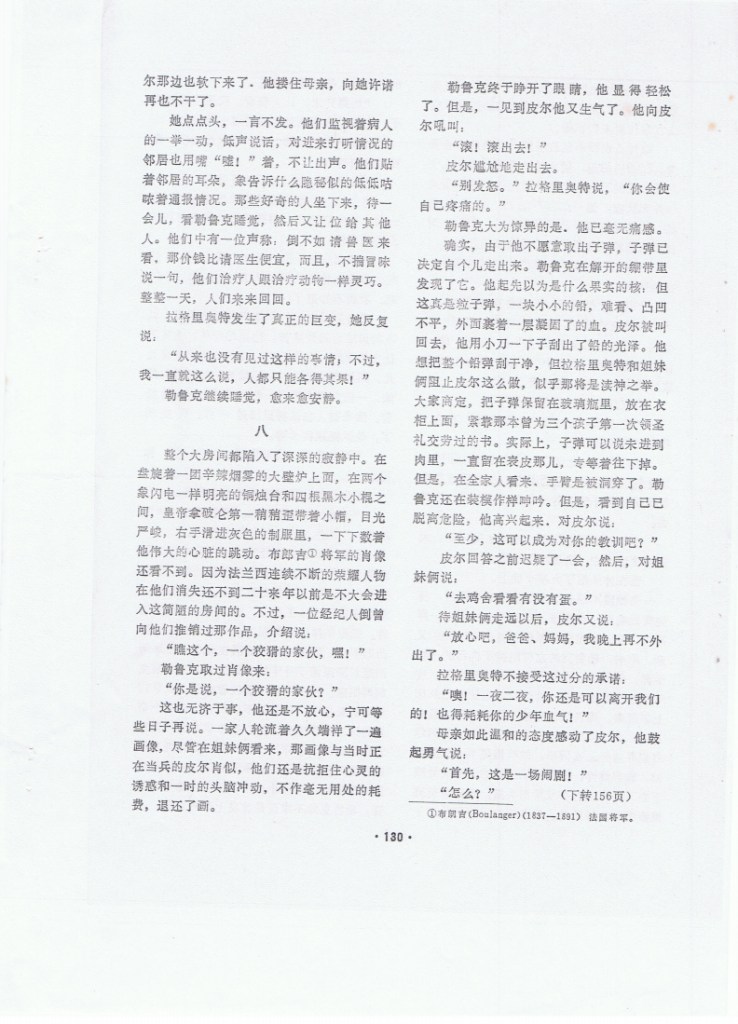追姑娘的人
〔法〕于勒•列那尔 苏应元译
于勒•列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胡萝卜须》《自然记事》等。“追姑娘的人”选自作家的散文小说集“冷冰冰的微笑”,写的是一对守旧、胆小的乡村夫妇煞有介事地管教已成年儿子的滑稽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译者
一
皮尔•勒鲁克刚结束了他五年兵役,认为自己已是个男人了,也就是说,工作之后,到晚上,就可以自由地单个儿外出,与人玩玩牌,有点输贏,同时讲讲部队的回忆;回家呢,也可以随便推迟些,直至街上空空荡荡、只有狂怒的狗将尾巴蜷曲在腿中间奔跑着,寻找骨头。皮尔本性温柔、听话,不过有点要充男子汉的小毛病,他不仅要在他的两位胆小、头脑简单的妹妹面前充大人,就是在父亲和母亲这两位可怕的双亲面前也不能自制。他母亲则立即警告他,
“我不让你喝过晩羹后离家。”
“可是,妈妈,我干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干,我!”
“小心点,不然,我给你一耳括子!”
一耳括子!皮尔耸了耸肩膀。他的母亲——人称短蒂樱桃“拉格里奥特”,在他服役期间并无什么变化。她似乎总是象过去那么瘦,甚至也总是那么好心肠。她爱她的孩子们,但方式奇特,往往显得可恶、生硬。然而,一旦儿子来信说“今夜我睡在警察所厅堂”或姐妹俩中的一个手指头不意刺出了血,她又哭哭啼啼。
“可是,妈妈,我可不再是孩子了!”
“住嘴,软鼻子!我禁止你追逐娘们,听到了吗?”
姐妹俩正在窗边专心缝补,任凭有弹性的凤呂草舌头随着每一丝微风斜着抚弄脸颊。她俩一听到这话,明智地低下眼。拉格里奥特发觉了女儿的反应,一下明白自己讲了蠢话,又迁怒于皮尔:
“首先,大无赖,在你的两个妹妹面前,你不能更自爱些吗?”
她的双眼在紧皱的眉毛下仿佛着了火。她攥紧拳头,浑身颤抖。她发白的嘴唇蜷缩在口腔里,针一般的牙齿把内唇膜牢啮着,边咬啮边往里拽,以聚成一块硬疙瘩。她快要抓起扫帚柄或锅柄了么?
姐妹俩直喘气,三针里有两针刺错地方。皮尔回答说:
“你并不懂得你在胡说些什么,算了吧,妈妈!”
他出去了,而且,这天晚上,他比平时回来得更晚。
二
父亲不得不干預了。这是一个有着非同寻常力气的男人。他曾一镐头揍在一头病公羊的脖子上,将其了结,人们据此得出结论,他可以抓住暴怒的公牛的两只角,就象翻转饭馆里的一头小乌龟那么轻易地让它四脚朝天。有一次,他不是仅仅腿膝弯了一下,就把他最好的朋友中间的一位的右腿弄折了吗?这些令人惊异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在冬夜的闲聊中,在夏夜聚会时,在雨蛙吵吵嚷嚷的歌声里,到处得到传诵,象传说般富有趣味。当然,他的男孩皮尔,高髙的身材,四肢象枫树既柔软又结实,明显地与他相象。但是,也有着怎样的差别呵!首先,一个儿子永远不可能象他父亲那么强壮。
勒鲁克在讨论到名誉问题时显得尤为可怕,不管这名誉涉及姑娘还是小子。他会突然身体肿涨,仿佛有一阵强烈的风通过血脉刮遍全身。人们还可望看到他的太阳穴处的血管在强烈的血潮冲击下“闪凸”,活象是那些由于受不了人们在周围有节奏地敲击而从湿润的泥里钻出来劣蚯蚓。对于淫荡之过失,勒鲁克只允许一种惩罚:死。
他已经准备用手枪一下干掉姐妹俩中受到不公正怀疑的那一位。幸运的是手枪未上子弹。机头扣到第六下才发出一个小小的、无用又滑稽的“哔剥”声。姐妹俩是完全清白的,枪杀发生时又肩并肩挨在一起,故永远也搞不清楚她俩中究竟那一位差一点会死去,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想开玩笑。由于他对可笑之事很敏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不过,他还是当场小心地装进了一颗子弹。到时候,一颗子弹就已足够。
三
他对皮尔说:
“看来,你在跟踪‘雌货’?”
“怎么,你也卷进来了?”皮尔回答说,“你,一个男人!”
这是难以忍受的,皮尔皱起额角,又固执地问:“你准备怎么样?”
“噢!我,”勒鲁克说,“我不会转弯抹角。晚上你要是还去找你的浪荡女人,你将尝到我的滋味。”
勒鲁克屈起手指,用三个不相同的姿势指指皮尔的胸膛正中,就象他是个确证无疑的罪人。
这一挑战激怒了皮尔。
他并不纠缠姑娘,但他要坚持自由。他要维护个人自由,维护自由追姑娘的权利。母亲找碴已使他情绪不佳。他淸楚所有和解的努力都将是徒劳。他化了一番时间寻找一个有力的答辩,并象小孩子在手指里揉捏雪球那样将答辩在脑海里来回琢磨,然后,他怀着恶意果断地把这个生硬的、紧凑的、十分执拗的答辩整个儿投到父亲的盛怒之中:
“我已经成年,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
姐妹俩停止缝补,双双竖起脖子,一个通红,一个雪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皮尔果敢地盯着他的父亲。两人肩膀前俯,气呼到对方脸上,准备碰撞。拉格里奥特大为惊慌,她看到儿子面临危险又一下子软了心肠,扑到两个男人中间,叫喊道:
“勒鲁克,你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对付这小子!还是让我来吧!”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尽管半弓着身子的勒鲁克本可以把新墙撞塌,他却乐于服从他的老婆。不知道是出于担心还是不屑于干,他克制住自己,对皮尔说:
“你在你父亲面前充汉子,我的小伙计,行!继续充下去,总有一天我会逮住你。”
说完,他象起重机搬运建筑石块一样慢吞吞地转过那威胁性的肩膀。
四
皮尔对这类喧嚷无动于衷,继续迟迟返家。他的母亲开始热衷跟踪他。她这么做有三个动机。首先,她是个虔诚的教徒,婚姻以外的纵欲在她看来只能是犯罪和堕落。她要当场捉奸,亲眼见证,并进行惩罚(因为在她眼里,皮尔仍是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子。使皮尔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然后,轮流提着他这一个和那一个耳朵把他拉回庄园。第二,作为母亲,她有嫉妒心。最后,她想当面见识见识那位多情小娘儿,采用巧妙的双打法,同样也给她那份应得的耳光。
皮尔一出门,她就拿起雨伞提上铁丝网灯笼设法踉踪。即使是最晴朗的夜晚她都带雨伞,而一到夜里,她不提灯笼是决不外出的。但要跟上儿子是不可能的。确实,皮尔腿长,不费什么劲就把她甩得远远的。何况他多疑、狡猾,故意乱拐弯。她很快就望不见他了,不得不怀着恼怒恶狠狠回去,却并不丧失勇气。勒魯克和姐妹俩已经睡了。三个人同睡一个房间。皮尔的床在屋子旁边的马棚里,紧靠牲畜。只要钯耳朵贴上墙,就可以听得见他回来的声音。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拉格里奥特伸腿跨越她的男人,卧到床和墙壁之间的狭条里。她仰面躺着,手抚弄着念珠,竖起两支耳朵倾听。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听不到门上的插锁声。不一会,她迷迷糊糊,就是门的“乒乓”声和母牛粪便断断续续的、低沉的坠地声也不可能分辨了。她只得把念珠挂到圣水瓶十字架上,熟睡过去。
有一天晚上,她大大吃了一惊。皮尔在一堵墙面旁突然消失,她很快就不知所从,只得十分忧郁地慢慢儿走回家。她听到有脚步声跟随她。似乎有人在谨慎地过来。她藏到一棵树背后。一个人影轻轻擦过。原来是儿子。怎么,如此之早?她沿着儿子的路线走去,小心翼翼窥视。皮尔径直走进马厩,避免在会踩出声音的石子上行走。他把木屐提在手上,轻轻地推门。正在这时,母亲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今晚你没有找到她?”
他显得很惊讶。
“怎么,你根本没有睡觉!”
看到她不吱声,他又高傲地回答说:
“是的,我没有找到她。”
“这么说,你承认了!你在追她,天天晚上追她!”
她已怒气冲冲,举起雨伞直戳他的胸脯,又狠狠地打他的胳膊,把灯笼震得象吊炉一样来回晃动。皮尔丢掉木屐,抓住伞头,低声说:
“你疯了,妈妈,你疯了,这是肯定的。”
她向皮尔投掷泥块、木片和一切能抓到手的东西。皮尔撑开伞,拋来的东西在绷紧的伞面上弹跳,发出响亮的声音。她用可卑的动物名称辱骂他,当然,她也担心会惊醒两个女儿,不敢过分喊叫。最后,她攥住了一根伞骨。皮尔一松手,就消失在黑夜里。
五
第二天晚上,拉格里奥特跟往常一样外出追踪。这一次似乎容易了些。他走在大路正中,头既不往右也不往左偏,就象是一个为散步而散步的正经人,无所畏惧。他平静地走进刺槐树的阴影里。拉格里奥特以为抓到了他,或许还能抓住另一位。但是,皮尔突然回过身来,叫喊道:
“别以为我没有看见你!不过,你是在白费吋间。”
他说完就跳过一堵干石块垒的小墙逃走了。拉格里奥特徒然叫喊: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他总是跑,身影在黑暗里渐渐远了、小了。好长一段时间,拉格里奥特还能看得见他在草地上奔走,踩着草儿,象疯了的幽灵。在他经过的路上,白色老牛儿都笨拙地站起来,伸伸站着露珠的冻僵的腿,费力地喘着气,样子很不安,牛角向前伸展着,闪闪发光,活象是被星星的光线张上弦的神奇之弓。
“我干了蠢事,”拉洛里奥特自言自语,“我过早暴露了。”
六
“这一次,他倆躲不开我了。”
她这么想着,远远地盯着皮尔来到河边。今晚,皮尔没有能甩开她。拉格里奥特总是耐心地在两行柳树中间行走。她不时地—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前。她暗自好笑,要是过路人远远地看见她这么进三步退两步的话,还会以为她是个跳着奇怪舞蹈的独脚演员呢!
皮尔在一个圆圆的河弯前面停下来。一支下浮子用的船儿被未上锁的链条系在一个柳树桩子上,船“啪啪荡漾着,犹如吠叫的狗舌头。皮尔解开链条跳上去。船向对岸滑去,下面是非常纯净的天空倒影,里面缀满明亮的星星,在行船的摇晃下象眼睛一样微微地眨个不停。水缓缓流着,没有障碍,在两行柳树的投影中间闪闪发亮,并流入树荫中。皮尔的篙子插下去又抽上来,静谧无声。他仿佛在月亮的光华下捕捞,用他那异乎寻常地伸长了的手臂在石子下面找鱼。
拉格里奥特不禁惊叫一声。运气又一次反过来和她作对。这么一走,她将永远见不着她——那个小娘儿。皮尔到了目的地。柳树在地上头摇摆着,织成目光无法穿透的绿篱笆,枝条儿在木堆上面东拖西曳。不用怀疑,他俩的调情之窝就在那儿,在木堆的后面,上面有新鲜树叶作亭盖。
拉格里奧特听得见皮尔说话,声音远远的不甚清晰,不时地被另一个她所听不见的回答所中断。她真想跳入水中;她气得喘不过气来,只能晃动她的两个拳头,叫骂着:
“浪荡鬼!浪荡鬼!”
她痛苦地哭起来。
七
白天,她着手侦查,不知羞耻地在整个村子里挨门挨户盘问姑娘。
“是你在想找公牛么?”
要是女孩脸红了,不敢表示听得懂,拉格里奥特就明确地问:
“我在问你,是不是你找公牛找到了我的皮尔头上?”
一位姑娘当面耻笑她,另一位不客气地把她顶回去,第三位姑娘甚至威胁要让治安法官拿传票来传讯她。
她什么也没有能打听到,对最终能否弄清真相感到绝望,越来越憎恨那位窃走儿子对她的爱的不知姓名的浪荡女子。而勒鲁克却并无反应,他一点也不在意,装得很超然。拉格里奥特于是刺激他出马,不过,对自己未能单独获得任何成功也感到羞恼。
“你也该管管了,勒鲁克,该结束了,这种风流事!”
“啊!你投降了。”勒鲁克轻慢地说,
“这没什么遗憾的。他把你捉弄够了吧?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对付他’的小子。噢!你,你还算是一个女中强手呢!最终你还是放弃努力了。行,轮到我了!”
他直截了当吿诉皮尔:
“要么你今天晚餐后立即睡觉,不然,我今晚就和你算帐。”
他的声音如此坚定,态度也如此强硬,姐妹俩慌里慌张,忐忑不安,四支眼睹象杂技演员的象牙球向各个方向迅速地转来转去。
皮尔甚至不予答理,他匆匆喝完羹,大摇大摆地出去,嘴里吹着口哨。
他在外头泡了大半个晚上。
当他漫不经心地走回他住的马厩时,身边突然响起一声爆炸。与此同时,发出一声高叫。皮尔冲过去,抓住正要往下倒的父亲。原来,勒鲁克的左臂刚挨了自己的一粒子弹。他象被人宰割了喉咙似地叫唤着。皮尔把他拽回屋里。一片惊慌。姐妹俩已从床上坐起来。她俩揉着眼瞭、张开嘴巴,脸色苍白,象小瓷塑象一样紧贴在一起。她俩尽力想弄淸是怎么回事。拉格里奥特穿着衬衫,面容憔悴,慌慌忙忙从她的大床高处滚下来。一束灰色头发滑出头箍,蜷曲着拖到她瘦瘦的肩膀凹处。勒鲁克的手臂可怜地下吊着。女人抚摸着跟他说:
“袒露开来,让人看看!我可怜的老头子,见鬼,你到底是怎么打这一枪的?”
但是,每触动他一下,他就挣扎着,嗄哑着喉咙呻吟:
“放开我。你们还不放开我吗?”
整个晚上,他象管乐队独自呻吟。但有一会,他安静下来,用孩子般的声音解释这意外的事件:
“我起先想开枪,后来,我又不想开枪,我在扣枪机的同时又制止自己…………..结果,我就不知道了!”
勒鲁克对自己的笨拙举动感到羞耻,又不能勇敢他忍受痛苦。他拒绝照料,尤其不让皮尔照料。在他看来,皮尔与凶手相差无几。姐妹俩站起来,一位端着摇晃不停的蜡烛,一位拿着布绷带,都脸色煞白、颤抖着,活象被人在冰桶里浸过一样。医生到了,他试图取出子弹。
“死也不干,这太疼了!过些时候,你再来!”
医生只好让子弹安静地留在原处。
“不过,要是他再来,那就等于出诊两次了。”医生走后,拉格里奧特说。
皮尔由于总是被赶开,不声不响留在屋角里,懊悔莫及。只有穿着便鞋的拉格里奥特有权靠近床。勒鲁克发烧了,胡言乱语,最后昏昏沉沉睡了过去。有时候,他挣扎着,把被单摔到床脚跟,把一双老树皮一样凸凹不平、颜色灰暗的腿露在外头。姐妹俩则赶紧深深俯下身干她们的活计,为了避免刺瞎眼睛,甚至不得不横拉着针线。全家轮流看护勒鲁克,静悄悄不出声音,对这个奇异的突发事伴感到神秘。拉格里奥特一边剪着包伤口的旧布碎片一边沉思。她评判皮尔的行为时更宽容了些。不管咋说,很可能他们过于把皮尔当作小孩子看待了。她并不怀疑,勒鲁克的不幸会是善良上帝的惩罚。皮尔那边也软下来了。他搂住母亲,向她许诺再也不干了。
她点点头,一言不发。他们监视着病人的一举一动,低声说话,对进来打听情况的邻居也用嘴“嘘!”着,不让出声。他们贴着邻居的耳朵,象吿诉什么隐秘似的低低咕哝着通报情况。那些好奇的人坐下来,待一会儿,看勒鲁克睡觉,然后又让位给其他人。他们中有一位声称,倒不如请兽医来看,那价钱比请医生便宜,而且,不揣冒味说一句,他们治疗人跟治疗动物一样灵巧。整整一天,人们来来回回。
拉格里奥特发生了真正的巨变,她反复说:
“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一直就这么说,人都只能各得其果!”
勒鲁克继续睡觉,愈来愈安静。
八
整个大房间都陷入了深深的寂静中。在盘旋着一困辛辣烟雾的大壁炉上面,在两个象闪电一样明亮的铜烛台和四根黑木小棍之间,皇帝拿破仑第一稍稍歪带着小帽,目光严峻,右手滑进灰色的制服里,一下下数着他伟大的心脏的跳动。布郎吉①将军的肖像还看不到。因为法兰西连续不断的荣耀人物在他们消失还不到二十来年以前是不大会进入这简陋的房间的。不过,一位经纪人倒曾向他们推销过那作品,介绍说:
“瞧这个,一个狡猾的家伙,嘿!”
勒鲁克取过肖像来:
“你是说,一个狡猾的家伙?”
这也无济于事,他还是不放心,宁可等些日子再说。一家人轮流着久久端详了一遍画像,尽管在姐妹俩看来,那画像与当时正在当兵的皮尔肖似,他们还是抗拒住心灵的诱惑和一时的头脑冲动,不作毫无用处的耗费,退还了画。
勒鲁克终于睁开了眼睛,他显得轻松了。但是,一见到皮尔他又生气了。他向皮尔吼叫:
“滚!滚出去!”
皮尔尴尬地走出去。
“别发怒。”拉格里奥特说,“你会使自己疼痛的。”
勒鲁克大为惊异的是他已毫无痛感。
确实,由于他不愿意取出子弹,子弹已决定自个儿走出来。勒鲁克在解开的绷带里发现了它。他起先以为是什么果实的核:但这真是粒子弹,一块小小的铅,难看、凸凹不平,外面裹着一层凝固了的血。皮尔被叫回去,他用小刀一下子刮出了铅的光泽。他想把整个铅弹刮干净,但拉格里奥特和姐妹俩阻止皮尔这么做,似乎那将是渎神之举。大家商定,把子弹深留在玻璃瓶里,放在衣柜上面,紧靠那本曾为三个孩子第一次领圣礼交劳过的书。实际上,子弹可以说未进到肉里,一直留在表皮那儿,专等着往下掉。但是,在全家人看来.手臂是被洞穿了。勒鲁克还在装模作样呻吟。但是,看到自己已脱离危险,他高兴起来,对皮尔说:
“至少,这可以成为对你的教训吧?”
皮尔回答之前迟疑了一会,然后,对姐妹俩说:
“去鸡舍看看有没有蛋。”
待姐妹俩走远以后,皮尔又说,
“放心吧,爸爸、妈妈,我晩上再不外出了。”
拉格里奥特不接受这过分的承诺:
“噢!一夜二夜,你还是可以离开我们的!也得耗耗你的少年血气!”
母亲如此温和的态度感动了皮尔,他鼓起勇气说:
“首先,这是一场闹剧!”
“怎么?”
(下转156页)
①布窃吉(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
刊《中外文学》(沈阳)199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