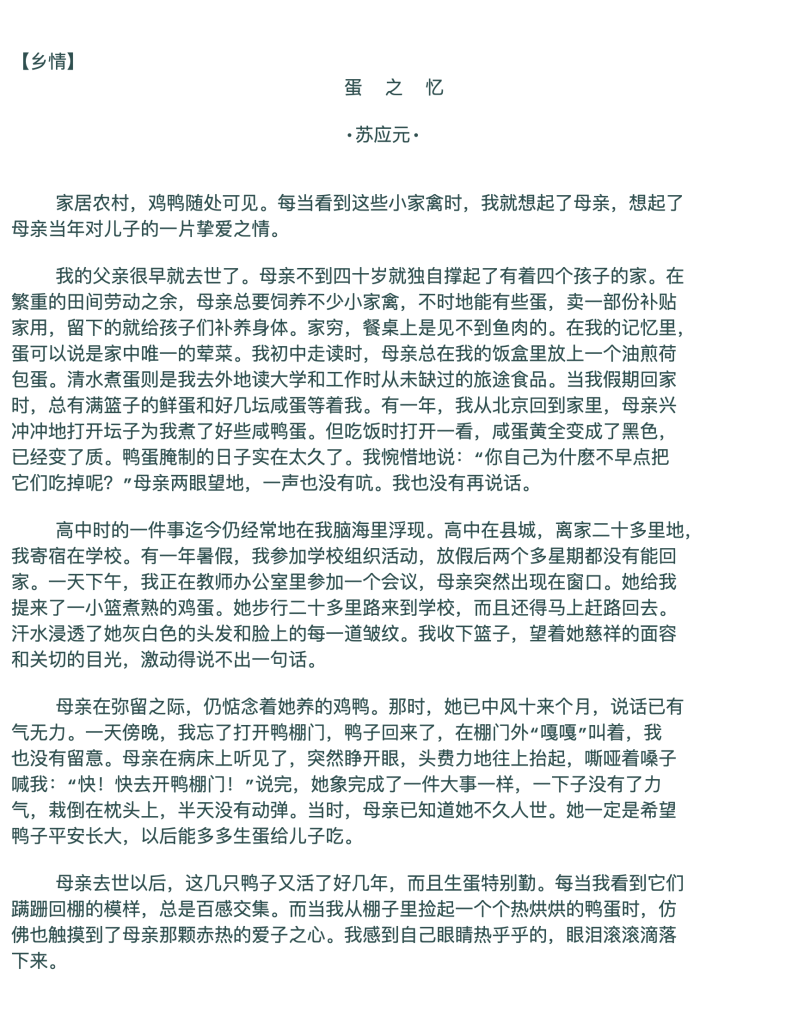苏应元
家居农村,鸡鸭是随处可见的。每当我看到这些小家禽时,我就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当年对儿子的一片挚爱之情。
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不到四十岁就独立撑起了有着四个孩子的家。但是,母亲在繁重的田间劳动之余,总要饲养不少小家禽,好不时地能有些蛋,卖去一部分补贴家用,留下的就给孩子们补养身体。家穷,餐桌上是见不到鱼肉的。在我的记忆里,蛋可以说是家中唯一的荤菜。我初中走读时,母亲总是不忘在我的饭盒里放上一个油煎荷包蛋。清水煮蛋则是我去外地读大学和工作时从未缺过的旅途食品。当我假期回家时,母亲也总是积聚了满篮子的鲜蛋和好几坛咸蛋等着我。有一年,我从北京回到家里,母亲兴冲冲地打开坛子为我煮了好些咸鸭蛋。但吃饭时打开一看,咸蛋黄全变成了墨色,已经变了质。鸭蛋腌制的日子实在太久了。我惋惜地说:“你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把它们吃掉呢?”母亲两眼望地,一声也没有吭。我也没有再说话,也并不需要什么回答。我很清楚,母亲是想留给儿子,她自己哪里舍得吃呢?
我念高中时的一件事,迄今仍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高中在县城,离家二十多里地,我是寄宿在学校的。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活动需我参加,放假后两个多星期都没有能回家。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师办公室里参加一个会议,母亲的面影突然出现在窗口。她给我提来了一小篮煮熟的鸡蛋。她是步行二十多里路来到学校的,而且还得马上步行回去。汗水浸透了她灰白色的头发和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我收下篮子,望着她慈祥的面容和关切的目光,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母亲在弥留之际,也仍掂念着饲养的鸡鸭。那时,她已中风十来个月,说话也已有气无力。一天傍晚,鸭子回来了,我却忘了打开鸭棚门,鸭子在棚门外“嘎嘎”叫着,我也没有留意。但母亲却在病床上听见了,突然睁开眼,头费力地往上抬起,嘶哑着嗓子喊我:“快!快去开鸭棚门!”说完,她象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一下子没有了力气,头栽倒在枕头上,半天也没有再动弹。当时,母亲已经知道她也不久人世。她一定是寄望于鸭子能平安长大,以后能多多生蛋给儿子吃。
母亲去世以后,这几只鸭子又存活了好几年,而且生蛋特别勤。每当我看到它们蹒跚回棚的模样,总是百感交集。而当我从棚子里捡起一个个热烘烘的鸭蛋时,仿佛也触摸到了母亲那颗赤热的爱子之心。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也是热乎乎湿糊糊的,抬起手背一碰,眼泪象串串珍珠滚滚滴落下来….
刊于“解放日报”1995年11月9日
刊于《未名Wei Ming Magazine》第十一期(WM9801)1998年12月总第11期


https://louisville.edu/journal/weiming/magazine/wm9801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