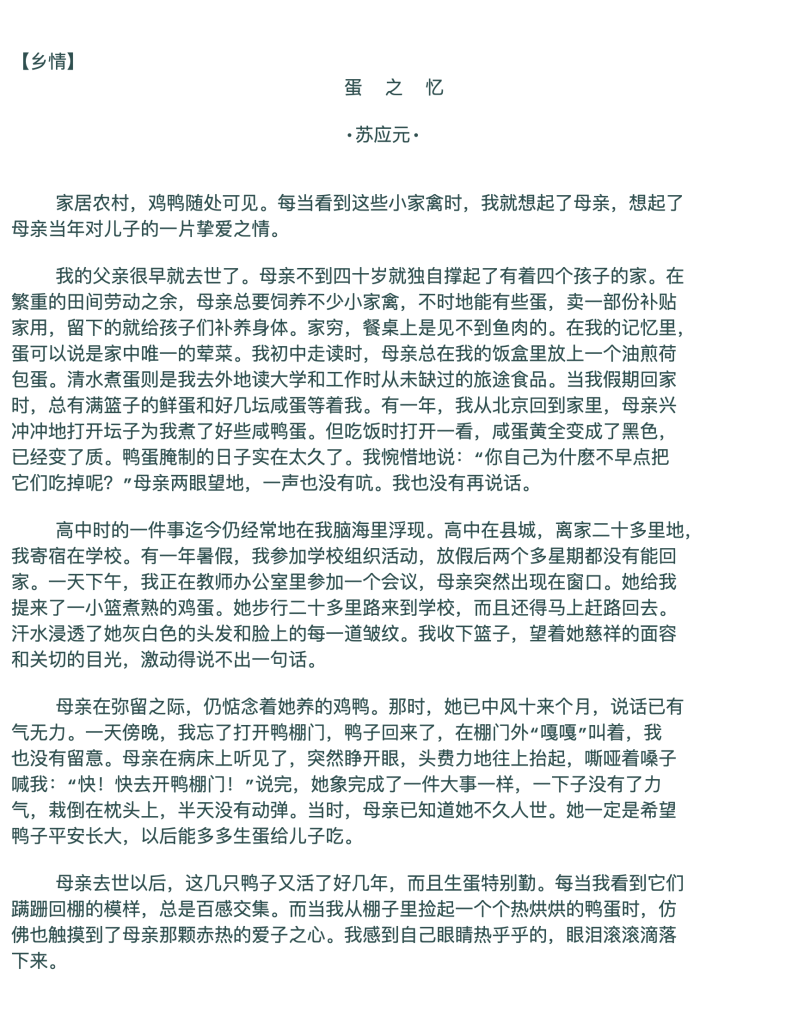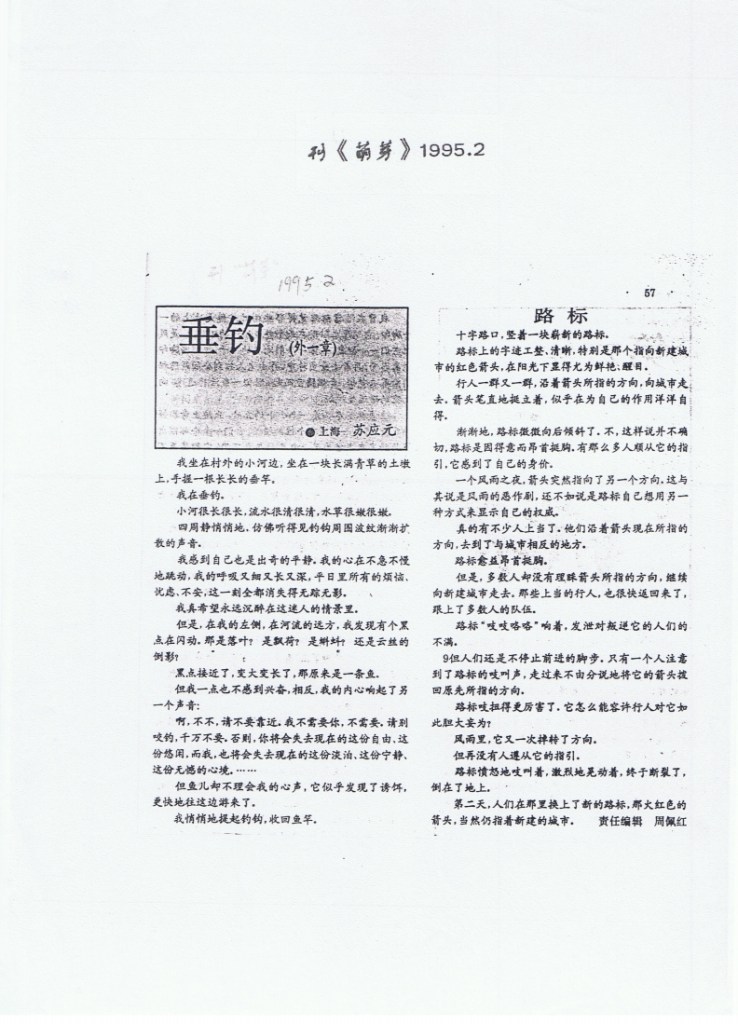苏应元
(原文已删: 从去年11月起,电子宠物繁衍日本,风靡欧亚。不仅孩子们乐此不疲,就是他们的父母叔姨们,也有不少迷恋其中,企图在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之外,寻找一分返朴归真的情趣。看着那么多人对着液晶显示器上的小小怪物如此沉迷的的样子,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饲养家禽的一段历史。)
家居农村,对鸡鸭鹅本不陌生。从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有饲养。不过,那都是母亲的事。后来,去外地念书工作,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也就渐渐淡漠了。中年回到故乡,才又重新有了接触,闲适之余,还萌生出自已动手饲养的雅兴。
脱壳未久的鸡雏,捧在手里,毛茸茸,软绵绵,热乎乎, 好叫人怜爱。它们都很怕冷,总是”叽叽”叫着挤在一起, 很有些想重新钻回蛋壳的劲头。不过,它们觅食却又显得十分老成,能迅速地从木屑中把碎米一粒粒啄起。我担心它们口渴,在旁边放了一盆水。起初,它们只是围着盆”瞿瞿”叫唤,相互探询着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过了好一会,才有一只似乎嗅出了什么味道,大着胆子伸长脖子把喙伸到了盆了里。马上,它得意地吸吮起来。其它十来只鸡雏当即跟上,金灿灿的小脑瓜一齐伸向盆子,脖子一俯一仰, 不多一会就把盆里的水吸吮干了。这以后,它们只要一看到小盆,就会 “吱吱”叫着拥上来,有的还不顾一切往盆子里踩。过了一些日子, 我将它们放到院子里。它们只犹疑了片刻,就全勇敢地追逐起草丛里的小虫和飞蛾来。只有在看到毛毛虫时,它们才又”瞿瞿”惊叫。它们喜欢结伴而行,一旦哪只掉了队,就会尖叫着寻找同伴,匆匆追赶。
两只小鹅也很可爱.刚放到院子里时,对外面的世界似乎很不习惯,总是想方设法朝我的两腿中间钻。阴雨天,地上长了青苔,走几步就要滑一跤,两蹼朝天拍打着,脖子晃过来又晃过去,很是逗人。它俩也是形影不离,旅途中,如果有一只逾越不了石块土坎等屏障,另一只即便过去了也会返回来。未久,它们就适应了外面的世界,开始离开小院,在村子里四处游逛起来.有一天 ,它们跑得太远了,到傍晚也不见回来,我哪儿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怀着一线希望,站到阳台上,大声发出平日里给它们喂食的呼叫:”咦–咦–“。真没想到,几分钟以后,它俩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摇摇摆摆地过来了。它俩似乎从我的呼唤声中感受到了我焦急的心情,那跌跌撞撞匆忙赶路的样子,真叫人难忘。
早晨,当我在院子里打太极拳时,总有一只母鸡在一边凝神望着我,那副安静专注的样子,犹如一个认真好学的学生。另有两只母鸡,只要见到我靠近它们,就会乖乖地俯下身,等待主人的抚摸. 而当我外出回来,也总会有几只鸡鸭跟着你走进院子,“咕咕”“呱呱”叫着.表示对主人的亲近。
有只栗色鸭,经常贪玩迟归。有一次,我疏忽大意, 在它回棚之前关了门。这以后,连续两天它都没有回来, 大概是以为主人不要它了。后来,我在村里村外找了好几圈, 才在村前一条河的鸭群里发现了它。我去到对岸,吆喝着将它们往岸上赶。但鸭群却只是沿河逃窜。我正在无可奈何之时,那只栗色鸭忽然离开鸭群, 爬上了岸。它显然已明白主人是在找它了。我高兴地走过去吆喝它回去。但是,它却坚持往另一个方向走。怎么回事? 难道它已经忘了回家的路?我加快步子撵它,它也越走越快,一直到了一个葡萄架下,才突然仃下来,”呱呱”叫了两声,钻进一个草丛里。我跟到草丛前,发现里面有两个鸭蛋。蛋是淡棕色的,一看就知道是它生的。我俯身捡起蛋。鸭子“呱呱”欢叫着,自动往我家方向走了。原来,鸭子是让主人来捡蛋呵。
可爱活泼的小家禽,给饲养者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不过,农村饲养家禽,成活率并不是很高。野猫、黄鼠狼、瘟疫之类,都是天敌。我第一次养的十来只小鸡, 晚上放在一只大纸箱里。一天,我没有将箱子盖压严实,半夜被野猫掀开了。 早晨我起来一看,满屋子鸡毛飘零,地上和窗户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纸箱里只存下最小的一只鸡,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瞿瞿”哀鸣着。从那以后,这只小鸡总是不仃地尖叫,一副孤零零无所归宿的苦怜状。我们吃饭时,它就跳到桌子下面的横木上,一直陪到饭后。平时,它也一有机会就跟随在人后。即使这样,它也未逃厄运。一次它外出觅食,被一只家猫一撵,连跳带飞跌进了粪坑里。
有只白颈鸭,长得特别肥大,走起来一摇一摆,十分笨拙。一天,它突然失踪了,直到天快黑时,我才在后村的一条污水沟里找到它。它大概是闯入了人家的自留地,被人逮住扭断了脖子,已经奄奄一息。不过,它的歪脖子仍向着我家的方向无力地伸展着, 拍打着沉重的翅膀。我把它抱回来,放到鸭棚口,它才一下子瘫倒在地 , 眼睛无神地望着我,渐渐失去了知觉。也许, 它因终于回到了鸭棚口而虽死无怨了吧。
当时,家里养着两只鸭,这只一死,另一只可惨了。它整天尖叫着东跑西窜寻找它的同伴,天黑了也不肯进棚。我不得不将它逮住关进棚子。它在里面扑腾着,头从棚栏缝中东伸西钻, 碰落了脖子上许多羽毛,看了真让人难受.
如果再逢上鸡瘟,那就更惨了。好好的一群鸡子, 会突然一只接着一只地死去。多少日子的辛劳,就这样一下子付之东流。
不过,只要你坚持不懈精心饲养,成功总是多于失败。当家禽终于长大,一到黎明,就有公鸡“喔喔”的报晓声, 打开鸭棚门,就有好几个鸭蛋等着你捡,白天,又常有生蛋后的老母鸡“咕呱”“咕呱”高声向你报告,这种情趣,这种意境,恐怕是没有饲养过家禽的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原文已删除: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之外,保留一份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返朴归真的 童心,人的生活中将增加许多的温馨和乐趣。)
通讯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南恒荣轧钢厂 蔡燕收转苏应元
邮编:201908
刊“东方城乡报”199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