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哥人


苏应元
多哥自一九六七年埃亚德马总统执政以来,经济上取得了较显著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六五年増加了七点三六倍,以人口平均亦增加了四点四二倍。
但是,从七十年代起,国际上原枓等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使多哥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另外,政府在前些年的经济建设中、也不适当地执行了“大工程政策”,兴建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工厂,大旅馆。这些大工企业或者由于管理不善、或者由于缺乏原料,多数开工不足,一些大旅馆入不敷出,靠国家补贴度日。例如,矗立在洛美市中心髙达三十六层的“二•二旅馆”利用率极差,毎月支出一亿西非法郎,仅能回收二千万。这都使多哥财政更趋困难,外债激增,至八十年代已达十亿美元。
针对这些情况,多哥政府作出了调整经济的决定。这些决定主要包括:
(一)加紧整顿国营企业和公司,要求国营企业和公司领导干部限期提出本単位严格的整顿计划、否则停止国家补站。无条件解散六个长期亏损单位,将另一亏损公司从公私合营转为私营。
(二)追查一些国营企业和公司经济亏损和管理不善的责任,要求失职人员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三)寻求国外技术援助,向友好国家聘请专家,帮助亏损企业和公司进行整顿、管理。
(四)要求将资金投放到最有效益的部门。
(五)进一步开展绿色革命,发展畜牧业。
几年来,多哥一直在为落实这些经济整顿的措施而努力。近来,多哥正把部分国营企业私营化作为企业整顿的重心。政府决定选择一些经过整顿可以赢利的企业交给私人经营。今年初,政府又把准备私营化的国营企业汇编成册,提供给外国政府和企业家做参考。

苏应元
科托努是贝宁政治、经济中心,全国第一大城市。
贝宁原来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波多诺沃,那是一个跻身于一片泻潮和丘凌之间的小镇,位于科托努东北三十多公里。一条土马路、几条小街、一个数百平方米的集巿广场,差不多就是它的全部建筑。置身其间,颇有一种窘迫感。
科托努则不然,它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恰恰是它的辽阔和舒展。我们的车子刚刚进入,城市西郊,一座大型建筑——贝宁体育场跃然入目。宏伟壮丽的体育馆、坦荡平整的运动场、碧水盈盈的游泳池,令人眉舒目展。离体育场不远,是科托努国际机场。瞭望塔高耸入云,机场跑道一望无边,大型客机银光闪闪,引擎待发发。人还未进入市区,就感受到这座新兴城市的宏大气魄。
科托努的市内街道大都宽绰、平直。西区中心大道穿过一个万米见方的广场,尤显开阔。广场是为纪念1977年贝宁人民击退雇佣军入侵事件建造的,中间有一个高台,顶端雞雕塑着勇士群像。勇士们手持武器,背靠背地屹立在大旗之下,警惕地望着远方,威武飒爽,体现了贝宁人民捍卫国家独立的钢铁意志。
一条大河洋洋洒洒,从北向南穿过城市,流入大洋。壮.阔的河面上,两座大挢遥遥相望,将城市东、西两部分连在一起。北边的大桥是贝宁独立后新建的,尤其壮观。大挢西侧是科托努集市大楼的方形白色建筑。楼外汽车云集,货棚目不暇接。楼里人群蚁聚,摩肩接踵。由矮墙围出的成百成千个格子间里,排满了售货小摊。日用百货应有尽有,花花绿绿的缠腰布琳琅满目。置身于这个当代建筑物庇护下的非洲传统集市,真是别具情趣。
离集市大楼不远处有一广场——五星广场。广场中央是一个五角星形的水泥建筑。在这个建筑之上,另有一个平行的小五角星形建筑。而在小五星形的建筑之上,还矗立着高达十几丈的五边形尖塔。站在这个建筑物上举目四望,各个星角所指方向,各有一条大道通向远方。朋友告诉我,五角星是新生贝宁的象征,这五条大道都将建设成城市的主要大街,待工程完毕,这里将成为科托努市的中心。

苏应元
美国总统夫人无需选举,也并无正式职权、但是、她们在白宫乃至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无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总统夫人进入白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白宫。她们几乎全都具有对前面一位夫人的布置推倒重来的嗜好。杜鲁门夫人曾耗费五百多万美元对白宫进行全面整修、布置、但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进白宫,就对原先的陈设翻了个样。里根夫人南希进入白宫后,也花费了八十万美元对白宫进行装修,唯有总统办公室由于里根的坚持才维持原样。
一些总统夫人还参与总统公务。杜鲁门总统就直言不讳,他在决定投扔第一颗原子弹和向朝鲜派遗海军之前,都曾征求过他夫人的意见,他还把他的夫人称之为“忠诚的合作者”。根据一九八七年的美国一项民意測验,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认为,里根总统夫人南希对丈夫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位第一夫人。由于白宫第一夫人的特殊作用,许多美国人对她们甚至比对副总统还关注。新当选总统布什夫人据说是个不爱表现自己的人,但她入驻白宫,又会怎样呢?这也是美国人很感兴趣的事情。

苏应元
在多哥首都洛美西北400公里的巴萨尔山下,有一座同名小城。城里城外,居住着一个三、四万人的巴萨里族。这个部族多数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流行着不少奇特的风俗习惯,有的颇能给人以启迪。
传说,巴萨尔原是上帝剖造的山神,后来他充当了这一地区的保护神,并将自己的名字赠予了这个地区和这里的部族。
巴萨里族除了信奉上帝与巴萨尔神外,对蝙蝙.蟒蛇怀有很深的敬意。蝙蝙由于能大量吞食蚊子被视为神物,对蟒蛇的崇敬则联系着—个久远的故事。据说,有个嬰儿因大人外出,在家里大哭不已。阵阵哭声打动了一条仁慈的蟒蛇,它爬近婴儿,用自己的尾巴当奶头让孩子吸吮,使孩子止住了哭声。
对好心肠蟒蛇的崇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萨里族人对孩子的珍爱。但是,他们对双胞胎却畏之如魔,认为那是大祸降临的征兆。两个婴儿,只留强壮的一个或男婴。另一个即被抛弃。生双胞胎的妇女也被視作不祥之人。
这种杀婴风俗,使人联想起古代希腊,罗马人为在艰苦的自然坏境中生存而采取的弃杀病弱、残废婴孩的习惯。在生产力低下、灾疫横行的古代社会,双胞胎一般成活率较低,这很可能是巴萨里人畏惧并择强者留生的最初原因。这类做法一旦涂上宗教迷信色彩,就不大容易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以至于一直延续了下來。
巴萨里人的男婚女嫁也留有远古时代抢亲婚俗的烙印。族中的青年男女订婚后,相互并不来往。但男方家长则细心察看姑娘的起居出没。新郎往往邀请身强力壮的兄弟、朋友借着傍晚或黎明前的昏暗天色,隐藏在姑娘经常过往的道旁,姑娘一旦经过,他们就一涌而上,把她扛上肩头载往男家,关在备好的房间里,六天后举行婚礼。
被抢的姑娘即使心甘悄愿,也应挣扎、反抗,大声哭叫,否则被认为缺乏家教。关闭期间,她还得设法逃回母家。姑娘一旦逃走,有可能几个月甚至整年足不出户,致使婚期大大推迟。因此,男家还要严加看守。
晚上,守卫新娘的年轻人猜谜、讲故事、组织达姆鼓盛会,为姑娘“排忧解闷”,那鼓声和欢歌笑语,预示着喜事将临。
第七天早晨,新娘按传统走出幽室,在村上姑娘们的陪伴下洗澡,并为亲属浣洗衣裳。晚上即举行婚宴。婚宴结束,全村欢庆。这时小伙子们尤其活跃,竞向姑娘们炫耀勇气和才能。有的在身上放上臼子,让姑娘们舂小米。有的头载兽角,模仿公羊抵墙。有的施展幻术,身上插着亮闪闪的刀子,院场上一片欢腾景象。
结婚是男子成人并成为部族正式成员的标志。从此,他可以在村议事会上取得发言权。平时,他打猎,捕鱼、耕种土地,是小家庭的主心骨。而一个已婚妇女,则更多地被看作是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按照传统,妻子终生不能直呼丈夫的名字。开始以她的一个兄弟的名字称呼丈夫,以后又用孩子的名字,称“XX他爹”;新娘过门后,马上接替公婆承担家务,还得上集市买卖小件物品,抽空协助丈夫种地。巴萨里族上述习俗,有的在今天还有着道德教育作用,有的已成为带有本民族特点的群众活动,也有的则因打上了人类原始时期的印记而显得陈旧,落后和野蛮。
刊《世界知识》1982年0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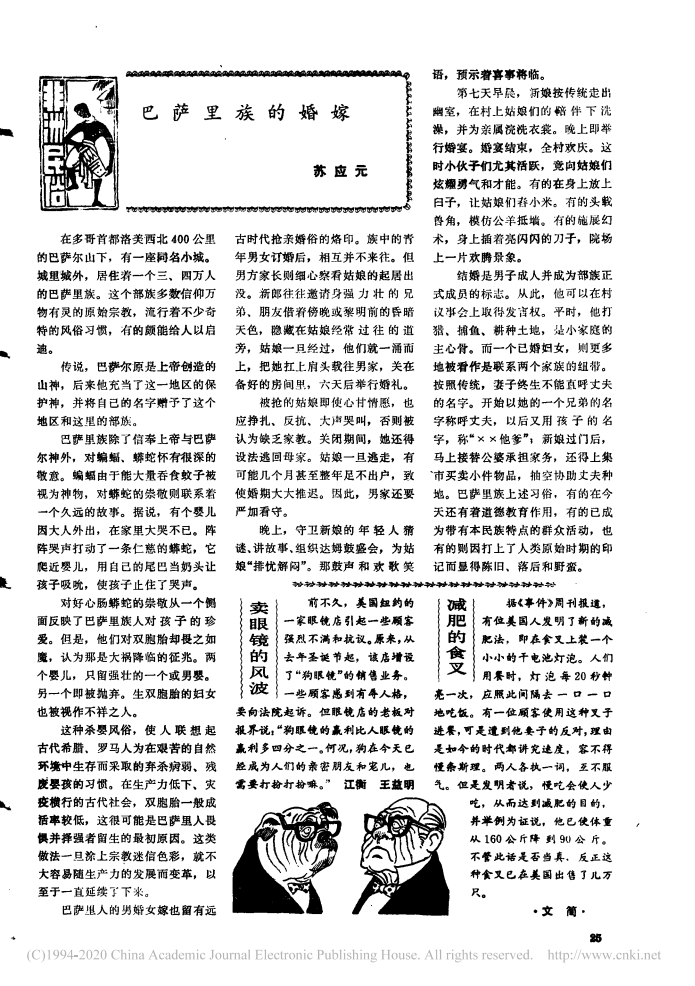
苏应元
60年代中期,美国飞机对越南和老挝日夜进行狂轰滥炸,我国驻这两个国家的外交机构,也经常成为它们轰炸的目标。1964年,在一次对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驻地的轰炸中,代表团成员多位负伤,髙云鹏不幸遇难。
1965年7月,我被派往老挝工作。代表团驻地在老挝川圹省康开市。我和同行的几个同志,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越南首都河内,然后由河内坐卡车到康开。赴任之途就充满了瑕险。7月18日,我们一行8人,由代表团团长朱英参赞带头,于傍晚乘越南车队的车子向老挝进发。河内郊外到处都是美机轰炸留下的弹痕残壁。清化市更是弹坑累累。越南最有名的清化大桥也被炸塌在江中,当地居民用装满泥土,石子的麻袋将缺口垫上,让车辆在夜间通行。为不让美国飞机发现目标,大桥上只有几盏小灯照明。我们的车队在微弱的灯光下,颠簸了20多分钟才安全通过。
一路上,差不多所有河流上的桥梁都已被炸毁,我们只能摆渡过江。有一次,我们行车大半夜,刚刚接近渡口,发现美国飞机正在那里来回盘旋,不得不又驱车数十公里,去另一个渡口。但那里连渡船亦已被炸掉。好在河面不宽,当地居民在渡口不远处为我们搭起了一座临时桥梁。我们赶在天亮前过了河。有一夜,车队出发不久,在一片空旷地遇上了美国飞机。美机扔下许多照明弹,像一长串灯笼悬挂髙空,把田野照得亮似白昼。飞机在我的头顶来回俯冲、扫射。由于是旷野,我们只能籍着田埂隐蔽自己。
公路上也随处可见弹坑。一辆车陷入坑中,四辆车合力才能将其拖出。遇到炸得不成样子的路面,车子只能一辆拉着一辆缓慢爬行。有好几次,我们在路中间发现美机扔下未爆的炸弹。为了抢时间,我们只能往前闯。星光下,汽车一辆接一辆,小心翼翼地在炸弹边上颠簸通过,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我们晚上行车,白天则停歇在树林里,将吊床在两棵树上一拴,躺在上面睡觉,越南的地方机关大都设在山林里。集市也在夜间,农民们靠着微弱的烛光照明,互通有无。有时候,我们也去集市补充一些瓜果蔬菜之类食品.
在芒新镇过河时,也是桥炸船毁,河边只有一只用木头、树枝、小舟捆成的筏子。筏子上面无法停车,我们只能舍车前行,由越南地方机关另派车辆在对面接应。我们分两批过河,不料前面一批过河离开后,迎接后一批过河的车辆遇到了美机拦截,我与两个同志只得半途折回,赶在天亮的退到树林隐蔽,与先行的同志失去了联系。我们只能各自赶路,直到5天以后,才在越、老边境相聚。
就这样,上有美机侵袭,下有未爆炸弹挡道,不是路毁,就是桥炸,我们整整走了42天,才于8月28日凌晨3点抵达康开市,创下了当今世界外交人员赴任时间最长的纪录。
代表团在康开的官邸早已被美机炸毁,放眼全是倒塌的房屋和弹坑。我去接替的法文翻译王永光指着残壁边的一个掩体对我说,当时,他及时跳入其中,才幸’免于难。掩体周围,还留有好多机枪扫射的枪眼。第二天,朱英参赞带领我们去为高云鹏烈士扫墓。墓地在郊区,没有墓碑,但坟上覆盖着很多新泥,表明最近刚有人为它添过土。我们几个也强忍悲愤,默默地用铁铲给烈士的坟头加土。
代表团已迁至离原官邸二、三百米外的一幢平房里办公,但我们到达两个月后,这里又遭受了猛烈轰炸,连我们修建在屋后的防空工事也被毁坏。代表团不得不将办事处撤往深山,住在临时搭起的茅屋里。但不久,美机又发现了代表团的行踪,整天在我们住地的山林上空盘旋。一
一个万里无云的上午,山后响起沉闷的飞机声。突然,随着一阵凄厉的呼啸声,数架美机从山头俯冲下来。刺耳的爆炸声立刻接二连三地响起来。树林间土石腾空,枝叶横飞。代表团住地出现好多弹坑。美机这次扔的是杀伤弹,弹坑不大,但弹片四飞,大部分茅星上都弹孔累累。有一个弹片,穿过茅屋泥墙,正好插在一个工作成员枕头上方三、四寸髙的墙面上。大家见了都唏嘘不已。
为安全起见,代表团同志在工作之余轮流劳动,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半山腰打出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坑道。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又搬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坡上居住,与大本营成犄角之势,以便出事时相互接应。
尽管环境艰险。但代表团成员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们搬来山中的第一天,就在茅屋的周围栽上花木,美化环境,后来,我们又在山谷里移栽了许多香蕉,果实成熟时怎么也吃不完。代表团的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两国的友好交往日益加深。
1966年初,我国云南杂技团不畏艰险,来到这里进行访问演出。为了避开美机的骚扰,演出场地大都设在深山里。虽然布景简单,道具也不那么齐全。但是,演出中那观众和演员感情交融的热烈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使我振奋不已。有一次演出,舞台就搭在康开市北边不远的山谷中,观众则坐在周围的山坡上。正当杂技演员们表演难度极髙的倒叠罗汉时,美国飞机突然出现了。随着一阵阵撕耳裂肺的俯冲声,爆炸声和机枪声在山背后震耳欲聋。山谷中惊鸟纷飞,野兔奔突,树叶果子纷纷掉落。但是,我们的杂技演员却镇定自若,继续分几层巍然倒立在山林中。两边山坡上成千名观众,也屏息凝视,纹丝不动。终于,轰炸和扫射结束,美国飞机凄叫着离去了。马上,鼓掌声、欢呼声响彻山谷。整个山林在斜阳下金碧辉煌,绚丽无比。
1966年12月初,我和一位同事回国休假,就在我两在河内等待回国期间,美机对河内又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我国驻越南大使馆也遭受袭击,当时,我倆住在使馆商务处,轰炸后赶往使馆馆舍,看到使馆的主楼被整整掀去了一个角。使馆的法文翻泽是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时的一个同事,他带我前往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也被弹片打穿了一个洞。
后来,留守老挝的同事告诉我,我走后不久,美国飞机又一次轰炸了代表团驻地,我在小山坡上的茅星亦被炸飞。后来,代表团又有几个同志,其中包括与我长途跋涉同去老挝的三等秘书李志学,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老挝的土地上。
(作者曾任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翻译)
刊《南方周末》1999年5月28日

苏应元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同事驱车离开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前往南方的沙里农庄参观。
农庄主吉丁加尔先生曾经担任过乍得政府的农业部长、过渡政府总理、代理过国家元首,目前退休居住恩贾梅纳,是中国使馆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去沙里农庄参观,也是他建议的。
乍得地处撒哈拉大沙漠边缘,景色比较袓犷,放眼望去,无垠的旷野上很少见到庄稼地,但临近沙里农庄时,出现一块块高粱地。
农庄住地在髙粱和绿色的树林后面,有两排茅屋,我们到达时,几个孩子正在门口玩耍。我们询向吉丁加尔农庄,孩子们马上说吉丁加尔就是他们的爸爸,这里就是农庄大果园。
果园紧靠乍得著名大河沙里河,种植最多的是拧檬树和桔子树,碧绿葱葱,不下好几十公顷。最引人注目的是芒果,一个个沉甸甸地髙挂枝头,比我们在恩贾梅纳市场上见到的大得多了。
果园管理非常精心,果树下、瓜地里找不到杂草。我们在参观途中,遇到好几个正在清扫落叶的农工。他们说,他们都是农闲临时来此打工的,一个月可得工资一万多非洲法郎,约合人民币200多元,虽不算髙,但补貼家用也够了。据介绍,吉的父亲娶了101个老婆,生了近千个孩子,吉丁加尔本人也娶过20个妻子。吉丁加尔家族是当地世袭酋长,他的祖父曾管理过96个村子,他父亲当了政府官员后,管理不了那么多,就让一些村子自治,自己管理56个。
临别时,果园总管送给我们好多水果。他说,这是他爸爸吉丁加尔让送的。车开了,果园里的大人小孩站在一起频频向我们挥手。真是一个兴旺、好客之家呵!
刊《新民晚报》1996年1月24日

蔡燕
几年前,随丈夫赴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一个使馆工作。使馆院子很大,有不少空地,我们几个家属,就在后院种起蔬菜来。
我们来自各地,各有各的技艺,没多久,一个个都成了种菜的行家里手。我种了几棵丝瓜,结的瓜密密麻麻,大院里的景致也为之增色不少。外交官们工作之余,都喜欢到菜园里走走,就像逛花园。一家的菜收获了,就分送给人家一起尝鲜,馆内的气氛也为之活跃了不少。
有时,我们也将蔬菜送给馆内的几个当地雇员,让他们带回去与家人品尝。他们说中国人的菜别具风味。他们有时开车外出倒垃圾,也会主动捡些牛粪回来给菜地施肥料。
我们的蔬菜有时还宴请外宾。有一次,我们夫妇俩请一对联合国官员夫妇吃饭,桌上有我种的黄瓜,那对夫妇对黄瓜冷盘赞不绝口,说久未尝过这么脆嫩香甜的东西了。那夫人还非要我说出是从哪个市场买来的呢。
刊《新民晚报》1996年4月17日

苏应元
非洲人对华友好,到非洲国家工作,就像是到了亲朋好友家中一样,可以说天天置身在友谊的氛围之中。
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我国驻多哥大使馆工作。多哥人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的态度,迄今难忘。在那些日子里,晚饭后我总要与一些同事去洛美街散步。暮色里,街上的行人、两旁摊贩、商店店员,总要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问好。尤其是那些孩子,常常一边兴奋地叫着“中国人!中国人!”一边赶上来与我们握手。星期天,我们去郊区散歩,顾便走访一些农家,也总是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苜都地区如此,边远地区也不例外。有一次,我与两位同事去多哥北方参加一项活动,顺便想看看当地一个少数民族的住宅,就冒昧造访了这个省的省长。省长一点也不因我们的临时打扰而显得不快,相反,他热情地把我们领进客厅,请我们在沙发坐,并马上让招待员倒酒倒冷饮。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又亲自陪我们去省军区司令家,建议司令派一名士兵给我们做向导。军区司令一边派人找向导,一边请我们在他住宅前的阳台上就坐。他夫人也很快捧出自制髙粱酒,用葫芦瓢盛了送到我们手上。不一会,一名士兵就应召过来了,带着我们驱车数十公里参观了颇具特色的唐贝尔玛族农民住宅。
一九九二年,我被派往我国驻乍得大使馆工作,也处处感受到乍得人对我们的友好情谊。由于我当过几任临时代办,还特别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的尊敬。当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轿车驶出馆外,沿途的警察都要举手敬礼,过路的行人也会自发地停下来行注目礼。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乍得,我从头至尾陪同,深深地感受到了乍得朋友对我国的热诚。代表团访问的时间较短,乍得外交部礼宾司长等动足脑筋,把日程安排得既内容丰富又十分紧凑。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晚上,乍得芭蕾舞团在当地最大的演出场所人民宫举行欢迎代表团的演出。演员们个个精抻饱满,热情洋溢,坚持要把乍得各个地区的民间舞蹈表现给代表团看,直到凌晨一点,演出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当时,乍得当局正在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人很忙,但乍得总统、总理和临时议会议长都希望能与代表团会面。由于实在拉不开时间,三个接见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当我们去总统府时,离代表团所乘班机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总统谈话言简意赅,乍得礼宾司也特地与机场进行了联系,保证了我代表团会见后一到机场就迅速办理好有关手续,按时登上了飞机。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如今,我已离开遥远的非洲好几个月了,但回想起这一幕幕非洲朋友对我们的热情友好的故事,心里总是说不出的感动,就像是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一样。
刊《新民晚报》1996年1月1日

苏应元
外交工作,并不总是与客厅、宴会厅相联系,其中也有着血和火的场面。
1965年7月,我与几个同志被派往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工作。代表团驻地在老挝解放区川圹省康开镇。当时,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和老挝解放区日夜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越南首都河内,然后由河内坐卡车到康开,赴任之途就充满了艰险。
一路上,差不多所有河流上的桥梁都已被炸毁。我们只能摆渡过江。有一次,我们行车大半夜,刚刚接近渡口,发现美国飞机正在那里来回盘旋,不得不又驱车数十公里,去往另一个渡口。但那里连渡船亦已被炸掉。好在河面不宽,地政府组织居民在渡口不远处搭起了一座临时桥梁。但桥面不很坚固,汽车无法载重通过,当地政府又组织了八十多人前来帮助我们卸车、装车,好不容易赶在天亮前过了河。
有一夜,车队出发不久,在一片空旷地遇上美国飞机。美机扔下许多照明弹,像一长串灯笼悬挂高空,把田野照得亮似白昼。飞机在我们的头顶来回俯冲。由于是旷野,我们只能藉着田埂左右隐蔽自己。还好,晚间能见度毕竟有限,炸弹都落在一、二公里以外。
公路上经常是弹坑累累。一辆车陷进去,四辆车合力才能将其拖出。遇炸得不成样的路面,车子只能一辆拉着一辆缓慢前行。有好几次,我们在路中间发现美机扔下的定时炸弹。为了抢时间,我们只能闯。星光下,汽车一辆接一辆,小心翼翼地在定时炸弹边沿颠簸通过,不能有丝亳的偏差。
我们晚上行车,白天则停歇在树林里,将吊床在两棵树中间一拴,就可以躺在上面睡觉。越南地方机关大都设在山林里。我们到都良市时,就在树林间的一间茅屋里找到了市委书记,由他组织人安排我们过江。集市也在夜间,靠微弱的烛光照明,我们有时也去那里补充一些瓜果蔬菜之类的旅途食品。
在芒新,也是桥炸船毁,河边只有一只用木头、树枝、小舟捆成的筏子。筏子上面无法停车,我们只能舍车前行,由越南地方机关另派车辆在对面接应。我们分两批过江,不料前面一批过河离开后,迎接下一批过河的车辆遇到美机半途折回,我与两个同志只得赶在天亮前退回树林,与先头的同志失去了联系,直到五天以后,才在越、老边境相聚。
就这样,上有美机侵袭,下有定时炸弹挡道,不是路毁,就是桥炸,我们整整走了四十二天,才于8月28曰凌晨三点抵达康开,开创了当今世界任何外交人员赴任的时间纪录。
代表团在康开的官邸也已被美机炸毁,放眼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和弹坑。新官邸设在二三百米外,两个月后亦遭受猛烈轰炸,连屋后的防空工事也遭到破坏。我们不得不将|官邸撤往深山,住在临时搭起的茅屋里。未久,美机又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整天在我们住地的山林上空盘旋。一个万里无云的上午,山后响起沉闷的飞机声。突然,随着一阵凄厉的嘘叫,数架美机突然从山头俯冲下来。马上,剌耳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来。树林间土石腾空,枝叶横飞。代表团住地出现了好些弹坑。由于扔的是杀伤弹,弹坑不大,但弹片不少。大部分茅屋上都弹孔累累。为安全起见,代表团全体同志在工作之余轮流劳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半山腰打出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坑道。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又搬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坡上,与大本营成犄角之势,以便出事时相互接应。
代表团先后有好几位同志,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就有一位与我一起赴老的三等秘书。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危险,代表团坚守岗位,坚持工作,为发展中国和老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刊《新民晚报》1996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