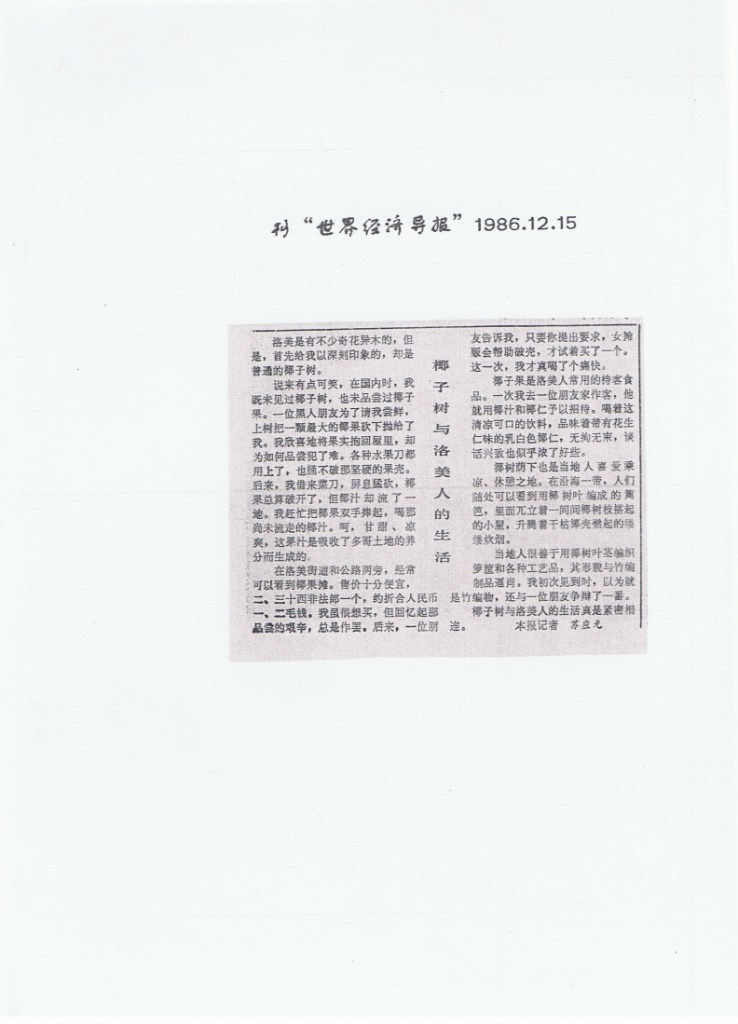国际和平年
苏应元
洛美是多哥共和国的首都,但同时又是一个边境城市。一九八0年我初到这个城市时,和几个同事在西头一条街上散步,无意中转入一条岔道,笑然发现前面有加纳路标,才知道已来到了边界线。
多哥和加纳的边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间的边界一样,形成于欧洲殖民者历史上长期的争夺和瓜分,往往并不顾及传统,地形,民族分布和重要城镇的位置。这类殖民者造成的畸形边界,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带来了不少问题和矛盾。多哥和加纳独立以来,也曾因边界问题多次发生纠纷和摩擦。我到多哥工作不久,边境关系又曾一度紧张,并导致一九八二年九月边界关闭。
一九八三年一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洛美西侧的阿弗拉奥边境点临时开放了四天。一月中旬,尼日利亚要求私自入境的外囯移民出境。不久,成平上万加纳移民离开尼日利亚,经过贝宁聚集到多哥东部边境。多哥和加纳两国政府防之进行磋商,决定自当月二十九日起临时开放阿弗拉奥边境点,让加纳移民返国。
二十九日傍晚,我与几位同志去阿弗拉奥边境点观看。但见十里长街,人群林立,男女老少全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移民车过来的方向。当一辆辆满载移民的大卡车经过时,满含同倩的目光一齐投来。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在阿弗拉奥边境点上。那里,移民车都要作短暂停留。每一辆车停下来,都有大批的人拥上前去慰问。这边,一个小姑娘正踮起脚尖,把提篮里的长条形面包送上车;那边,一位老年妇女提着沉甸甸的水壶,把一杯杯水送到争着伸下来的手里。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动员,谁也不认得谁,但谁也不觉得陌生。当卡车重新启东时,车下的人挥手送别,高声祝福;并唱起节奏强烈的歌。看着这一情景,我和同去的几个同志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都深深地感到,边境两边的人民亲如兄弟,尽管两国间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由于这种深厚的情谊,边界不可能长久关闭。这一次阿弗拉奥边境点的临时开放,很可能是边界正式开发的前奏。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两国所有边境点终于全部开放了。当天中午,我就和一位同志赶往阿弗拉奥边境点观看。那是何等热闹的场面呵!早先冷落的边境集市重新兴旺起来。通道两面彩色的太阳伞象雨后蘑菇林立,伞下支起了数以百计的售货小摊。正等着过境的小汽车,排成一字长龙。人们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无数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也都排着长队,从两国的边境检查站鱼贯通过。
出于―种怀念之倩,回国前,我与几位同志又一次到边境大街的那条岔道散步。迎面过来一位加纳靑年,「你们想去加纳那边走走吗?」他微笑着问。「可以过去吗?」我们反问他。「可以,只要向哨兵打个招呼就行。」说着,也不管我们是否真想过去,就带我们从一条小路走到一个村庄前面。村口,一个军装齐整的加纳士兵正在和几个农民围坐在一起打牌。青年告诉他我们的来意后,士兵笑着说:「你们身上有武器吗?没有?那没问题,请过去就是了。祝你们一路偷快!」看来,边民过往已经完全自由。
我们沿着岔道走了一段。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原野上,白薯地和木薯地一片又一片,中间耸立着芒果树、椰子树和猴面包树。几个农民,.男的手提短锄,女的头上顶着装白薯的棕筐,正向着远村走去。这和多哥的农村景色毫无二致。边境两边的农民,也真是难以辨别的兄弟姐妹呵!
而后,多哥和加纳两国的边境关系继续得到改善。看来,在两国人民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殖民者遗留给他们的矛盾、纠纷,终有一天会成为历史陈迹。
遥祝多哥和加纳的边界永远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边界!
刊《中国市容报》1986年3月6日